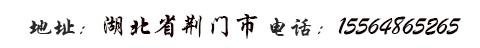浅谈中药功效在认定理论上的局限性
| 刘军连出诊时间和医院 https://wapjbk.39.net/yiyuanfengcai/ys_bjzkbdfyy/793/中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中药功效的发展除依赖于用药实践外,还受到中医理论的制约。即药物的应用需经中医药理论“加工”才能最终上升为功效。随着用药经验的积累,主治范围的扩大,一些药物作用由于与传统认识或基本理论发生冲突而不能上升为大众所能接受的功效。例如大蒜,从《名医别录》始即认为“性温”,《医林纂要》等甚至认为“性热”,但大蒜对湿热痢疾疗效可靠,对于热毒疮痈,内服外用均有较为肯定的疗效。但因其药性温热,对于前者,不可能认定其具有““清热燥湿”功效,对于后者,也不可能言其有“清热解毒消痈”之类作用。出于相同的原因,药性辛温的薤白,虽然对于湿热痢疾,单用即可获效,对此早在唐代的《本草拾遗》便有记载,至今只能称其治疗痢疾可以“行气导滞”,其实,这对薤白来说,只是一种辅助的兼有功效。又如几乎所有中药著作均认为牛膝引火(血)下行,治疗胃火上炎的牙龈肿痛、口舌生疮,气火上逆,迫血妄行的吐血、衄血,肝阳上亢的头痛、眩晕。按照中医理论之治则治法,治疗胃火偏盛的功效应是清胃火,治疗血热妄行的吐血、衄血的功效应是凉血止血,治疗肝阳上亢的功效应是平肝潜阳。牛膝确能治疗以上三种证候,但发挥的功效却不是清胃火、止血与平肝潜阳。对于这些应用,怎样进一步归纳出功效,可能有待理论的深化与突破。又如,远志功效项下的“消痈肿”,实际上只是主治,而不是真正的功效。虽然其疗效古今认同一致,只因其药性偏温,不得已而如此沿用不尽人意的表述。麝香、蟾酥,治疗热毒疮肿,不论内服或外用,无疑皆是要药,也是受“热者寒之”理论的制约,麝香采用“活血消肿、止痛”立论,蟾酥则据“以毒攻毒”入说。再如,乌梅与诃子,药性收涩,对久泄泻痢,正已虚而邪不甚者,发挥“涩肠止泻”功效。而对痢疾之初,正盛邪实,单纯收敛之品有“闭门留寇”之嫌,故宜禁用。然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本经逢原》称乌梅“今治血痢必用之”。临床应用表明两药对痢疾早、中、晚期均有较好作用。怎样看待乌梅、诃子治痢作用?在“涩肠止泻”不能包容这一主治时,应当如何补充新的功效,也急需回答。这里除了理论制约以外,还有一个认识的误区。人们常常将性状(即真实滋味)的酸涩与性能的酸涩混为一谈,错误的认为凡是有酸味的药一定具有很强的收敛固涩作用,乌梅滋味甚酸,自然得出以上的结论。其实并不难发现,中药里面收涩敛邪作用最强的药是罂粟壳、洋金花等品;而酸味浓烈的乌梅、香醋等,根本不易敛邪。可见,要深入研究乌梅等药的未尽功效,首先要克服该认识误区。另外,金元时期以来,临床论治模式从辨病或辨症论治为主转向辨证论治为主,淡化了人们对病的研究,阻碍了中医对病认识水平的提高。对药物作用的观察也从“对病”或“对症”的应用转而重视“对证”功效的总结,这种转变又形成了后世“对证”功效为主流的中药功效网络。客观上造成了“对病”应用不能向“对病”功效转化,没有形成“对病”的功效系统。而“对证”功效与“对病”功效在临床却相互不能取代。从“异病同治”的角度去审视两类功效,因辨证施治原则要求,只要“证同”,病虽异,治亦同。然而不同疾病有不同特点,即便“证”同,由于各疾病在发生发展上的差异,必然在同“证”后面隐藏着不尽相同的因素。“对证”功效在遵循“异病同治”时,不可避免地要忽略疾病的特殊性。“对证”用药在治疗上有其所长也必然有一定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应当由“对病”功效予以弥补。但证治模式的转变致使“对病”应用仅被内化为“对证”等功效而并没有独立地发展起来。后世功效系统对药物应用经验的归纳并非完美无缺,药物主治升炼受理论制约,一些临床卓有成效的应用,因在“证”或“症”等方面难以找到直接的联系(如桔梗“主腹满肠鸣幽幽”、威灵仙治“诸骨哽咽”),从而不能上升为功效。经验仍以主治的形式流传,而功效项对这些应用的概括缺如。而随着功效在临床中药学核心地位的确立,人们已习惯从药物功效入手选药,这又不可避免地造成对那些尚未上升为功效的应用经验的遗弃,致使一些宝贵的用药经验失传,这不能不说是一重要原因。这种传统中药功效所反映出的在理论上容量的不足主要是一门古代科学相对于现代科学显现的局限,是历史的必然。由于现代科学的介入,新方法、新手段及新仪器等被广泛采用,以及药物新剂型的引进与研究,中药新功效也在不断被发现被认识。可以预言,随着现代科学理论的渗透,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现代科学术语成为中药新功效的内容。而这些术语往往没有合适的传统功效语言可以替代,如苦参升白细胞,青皮、枳实升压抗休克,泽泻、山楂降血脂,罗布麻降血压,这些功效将与传统功效术语并存,也是中药功效发展的组成部分。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egenga.com/jgzz/13298.html
- 上一篇文章: 四川神农祥农茶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