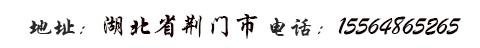支疆故事白白的桔梗长满山野
| 北京治疗白癜风 http://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白白的桔梗长满山野——献给那些支疆的无名英雄文/张张老白生前照“桔梗哟、桔梗哟、桔梗哟、桔梗,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只要挖出一两棵,就可以满满的装上一大筐。哎嘿哎嘿哟、哎嘿哎嘿哟、哎嘿哟,这多么美丽、多么可爱哟,这也是我们的劳动生产……”这是我在整理电脑资料时,找到的一段年我在吐鲁番英萨村驻村时拍摄的视频。画面中是位84岁的支疆老人,头发花白,面容消瘦,一袭藏蓝色老式中山装。他唱的是一首朝鲜民歌,唱歌时脸上始终保持慈祥的微笑,声音像极了风吹戈壁的回响,苍然有力。如今,虽然老白已去世两年,但关于他的许多事却如这歌声一样久久回荡。老人叫白本云,村里人都爱叫他老白(bei)。老白是吐鲁番市英萨村第四村民小组的村民,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汉族住户。老白年参加抗美援朝 ,年入疆参加支援边疆建设,从此在吐鲁番扎下了根。在驻村时,基于“好男儿应当为国家而战死沙场”的热血情怀,激起了我对老白的浓厚兴趣,所以,我时常到老白家入户“搅扰”。 次上门搅扰,是刚过罢春节,村里还是一派硬生生,到处像长满了冰刺儿,绕村而行的坎儿井水还冒着吐烟似的热气。然而,老白却端坐在门前的石板上,一身藏蓝色的老式中山装,手里夹着“唢呐形”的莫合烟,身边依着一根手杖,默默盯着门前泊油路上稀疏的人流车流。我上前问好,老白有点耳背,把脸侧向一边,他的侧脸、脖颈、耳蜗爬满了老人斑。我又大声问了一遍,老白才慌着点头回道:好啊好啊。露出一口假牙转而,吃力地起身,邀我进屋。平凡无奇,这是老白给我的 印象,但也终成永恒。在与老白的几次交谈中,我发现从他的记忆挖出那段战争岁月并不容易。或许是因为老白年事已高,他的每次述说总是断断续续、反反复复。他只零星的记得:援朝时他隶属于后勤排,挖战壕,清路障……所背的枪是莫辛纳干步枪……和朝鲜妇女一起在后方为前线战士送粮食,朝鲜妇女能用头运送百斤重的粮食…… 的炮弹12千磅,炸出的炮弹坑,有一辆解放车那么大……朝鲜人喜欢在河边点起火堆跳舞唱歌,喝自酿的苞谷酒……每次交谈,老白的儿媳会一直守在老白身边,把我们的谈话用大声调互相转述,并时刻观察老白的气力,每觉察到老白陷入沉默,她便扶着老白到屋里休息,我们的交谈也就到此为止,每次交谈不超过20分钟。翻过四月,天气确定暖下来,村里的桑葚随风像果糖一样“啪啪”地砸向地面,一颗颗绿宝石似的青杏也挂满枝头。老白的行动比初见时更显吃力,记忆也越发模糊。对他来讲,似乎该回忆的事全部述说完了,每次交谈,重复和沉默两样都越发的冗长。我便以为在老白身上再无可挖掘的事情了,“搅扰”的次数渐少,只是偶尔到商店买些核桃粉、酸奶之类的前去看望。一天,四组组长到村委会告诉我们老白住院了。我们愕然,医院,走进病房时,老白已经做完肿瘤切除手术,表情安详地躺在病床上,手上输着液,均匀的呼吸将他蓝色的病号服带出节奏的微漪。老白的儿子一直守护在病床前,双眼熬得通红,看我们来,脸上露出牵强的笑。我们没有惊扰老白,就守在一旁等他自然醒来。不久后,老白的儿媳手里拎着粥和包子走进病房,见到我们,眼泪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她说:“这几天天天担惊受怕的,生怕老爷子……受了罪不说,还……”说着,声音颤抖起来:“老爷子岁数大了,后期的化疗身体扛不住,只能接回家了……”话没说完已经泣不成声。我心里清楚老白所剩的日子不多,虽然不能这样想,但现实总是硬的让人无能为力。老白在家休养的日子,我每天都会前去看望,陪他说话闲聊,有时一句话不说的坐着,只是和他默默地吸莫合烟。端午节那天,老白精神头突然反常的好,或许是因为高兴,交谈中老白破天荒地哼起了歌,那是我 次听他唱歌。我问:“这是什么歌?”老白说:“是援朝时跟当地朝鲜妇女学的。”我说:“好听!”老白便大声地唱开了:“桔梗哟、桔梗哟、桔梗哟、桔梗,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我恍然掏出手机把这珍贵的一刻录下来,但老白唱到一半却不唱了,目光里闪过了一丝忧伤,他说:“当年有个朝鲜妇女唱这歌特别好听。”又说:“那是个了不起的妈妈,在援朝快结束时,美国鬼子反扑,我被炸伤随当地群众一起转移,中途遇到扫荡,我们躲进一个山洞里,那个妇女为了掩护我们,让自己的儿子背着我的枪穿上我的衣服冒充 把敌人引开了……”哀伤彻底爬满了老白的脸颊,他沉默了许久才说:“那个小伙子只有十几岁的模样……我们坐车回祖国时,路上大家都哭了,因为我们没死,因为我们的活是用别人的命换的……”说到这,老白有些激动,呼吸急促起来,老白的儿媳赶紧扶老白进屋休息。从那以后,老白的身体每况日下,我仍每天前去看望。每每去,老白依然坐在门口的石板上,但已不是端坐,头沉沉地耷在肩上。他身上仍是那件藏蓝色的老式中山装,因为天气热,领口解到了第二颗纽扣。手指间夹着卷好的莫合烟,可能是忘了点燃,一直夹着。而依在他身边的手杖,这么久了,我才发觉到手杖的表面被他多年的拄握已磨得像镀了一层蜡。我们见面再无别话,只是并排坐着,默默地盯着门前路上的人流车流,“叭叭”地吸着莫合烟。七月的一天,老白终是未能战胜病魔,驾鹤西去。老白下葬的那天,村里的天空充斥着悲伤,闷沉的日头蔫吧地埋在厚厚的云层后面,空气的颗粒凝固似的浮着,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老白子孙们的哭声。到了下葬的时刻,云层压得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抓住,几缕风跳过枝头,重重摔在了地上,已经能闻到潮湿的气息,却还是没有雨的迹象。送葬人群默默地向坟地方向推移,然而,每个人却都像淋透了雨,拖着沉重的身体。老白的遗物极简,给我留了一包他未抽完的莫合烟,给后人留了一枚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年的标有全国通用粮票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粮票。除了这些再无其他,似乎老白的一生就是这寥寥的几个物件。我不甘心,所以在老白去世后,我从新梳理每次与老白交谈的内容,打算为他写一篇关于支疆老人援朝的回忆录,但总是提笔又搁置了。我对老白太不了解,我甚至怨悔没能提前一年驻村,如果早来一年,或许老白的大半生就能被完整地记录下来。后来每次在四组入户,零零总总的能从村里的老人们口中听到老白生前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和老白一起奋斗过的人,做过机修、修过渠坝、修过路、一起掏捞过坎儿井、一起战风沙开过荒地。说起老白,他们的语气中充满了敬意,他们说:“如今村里虽然泊油路修上了,富民房住上了,家家户户有羊有车,但是如果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像老白这样的支疆人,哪有眼下的好日子……”我把他们说的一一记录下,已然不是为了写老白,而是为了不能忘却。上世纪50年代,为了开发和保卫边疆,国家动员大批内地青年支边新疆。到了60年代,“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主旋律。年,退伍后的老白凭着曾是军人的一腔热血毅然从张家口一路向西,来到吐鲁番扎根落户。在那个生产技术人才匮乏的年代里,村里人或许连喷油头、轴塞、活塞、缸套都闻所未闻,老白靠着在援朝时学到的机修技术,修好了村里 台水磨坊里的柴油机,从此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老白的机修技术在村里被奉为神奇和魔法。在多年后的回忆中,村里的老人们对此仍是赞不绝口,他们说:“本来像废铁一样的东西,只要经过老白的手,都会像鸽子一样飞起来的。”很多时候,村里人又为老白感到惋惜,说他是“勺子”(新疆方言傻子的意思)。由于老白的机修技术独秀一枝,县上水管站的人想调老白进城,那个年代进城就等于有了“铁饭碗”,可老白并未同意,而固执地待在村里将自己机修的手艺白白地交给别人。别人给他粮票做酬谢,他也婉言谢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后来,老白教会了很多人,自己却“失业”了。老白为了养活一家老小,跟队上的人去掏坎儿井。掏捞坎儿是要命的活,每次掏捞都是从死门回到生门的过程。村上的 的一次坎儿井塌方事件是发生在年,春灌迫在眉睫,但是坎儿井大面积塌方,造成井水断流。按照以往经验,疏通上下游,只能一个人下到井底,爬过狭窄的横井,到达塌方区,凿出通道。然而,谁都知道,塌方处一旦凿开孔,积水无疑会像泄洪一样,那个下去的人,生还几率几乎为零。这种事村里人都避之不及,老白却主动请缨,他让井上的人用麻绳绑住他的一条腿,自己带着刨器,交代井上的人,只要他一凿通,扽一下绳子,井上的人就把他往外拉……如今,坎儿井水如同流绸一样闪着光涓涓地流淌着,老白身上因那次掏井留下了几十处疤痕却鲜为人知。在后来的许多次入户中,老白的“支疆岁月图”逐渐在我面前展开,他是机修的“能人”,是不愿吃铁饭碗的“勺子”,是掏捞坎儿井“拼命三郎”,是战风沙开荒地“把式”……不一而足。老白的支疆岁月令人唏嘘不已,又令人肃然起敬。“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此时此刻,当我再次看到老白在视频歌唱,那如同风吹戈壁的回响的歌声,不禁让我眼眶潮湿,忽然想起老白说的那个了不起的朝鲜母亲和那些因为死去的战士而感到内心负疚且活着回到祖国的战士们……我似乎寻找到了老白支疆的答案……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egenga.com/gcjg/6236.html
- 上一篇文章: 日本绘画大师铃木辉实的水彩画配色心得
- 下一篇文章: 三等奖文评丨饮食男男by桔梗人生唯爱